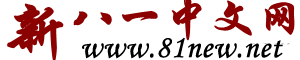第一百二十九章 恩仇
作品:《行医问缘》 “成国侯?”陈夫人看了丈夫一眼,很快想到了什么,眼神也犀利起来,“对了,慕容钦,可那小侯爷今年不过二十有三,会见多识广到认得出断锋剑法吗?”
“自幼习武又能在老侯爷没了后一力接下平南军这个担子,此子少年老成,不得不防。”陈娴道,“不过他至今不曾有过任何表示,未注意到也未可知。”
“是我大意了。”陈夫人叹道,随即愤然,“可我夫妇二人好歹救了他一命,就算他看出了什么,若去告发岂非恩将仇报!”
“慕容家老侯爷慕容舶,年轻时被断锋剑法伤过。”陈娴突然道,“而且,是伤在我剑下。”
大家齐刷刷望着陈娴,一时噤声。
片刻,陈武师深吸一口气,大着胆子问道:“母亲,孩儿能斗胆问一句……为何伤他吗?”
“哪有那么多为何?”陈娴皱了皱眉,“那时我师父是厉王的人,他慕容家是如今官家的人,夺嫡之乱里两军交战,伤到人有什么奇怪的。”
陈娴说着,抬头敛目,仿佛在回忆往事:“老成国侯那时也不过是个年青将领,他的功夫我并不放在眼里。但慕容家最擅水战,世家中子弟皆水性精熟,慕容舶也一样。”
“我和他短兵相接,与他交手,被他拖下水去,险些溺毙。最后,我将“寒霰”下在水里偷袭了他,方才将他重伤,我得以逃脱。”
“寒霰是由冰蟾为引、密蒙花、谷精草等极寒至凉的药材炼成的,入水和之,寒凉侵骨,无孔不入。”我回忆着君清澜留下的典籍记载,“若武者调动内息抵御,则寒气立刻反噬重伤经脉。”
“不错,寒气一旦入体,若无法根除,则日后再有损伤,伤口愈合也会变得极为困难。”陈娴道,“当初此药是厉王身边的用毒高手所制,我并不擅毒,用寒霰也是情势所逼,况且道不同不相为谋,我又并非多仁义的人,这事虽做的不光彩,我也不曾在意。”
“然而,直到来了京城,我才听闻慕容舶已死,死因是追击海盗时旧伤复发,而且没能挺过去。”陈娴叹道,“我听说,他为华国守了一辈子海疆,原配耐不住寂寞和离而去,所以他一生仅有一子,便是如今的小侯爷慕容钦。”
陈夫人道:“这慕容小侯爷,我见他时便觉他体质过于阴寒,性子也冷,或正是……受了寒霰的影响罢。”
陈娴苦笑了一下:“阿辞,我已这般大的年纪,而今回想,虽不说后悔,但若是不得善终,我也并无怨言。”
“祖母,您别这样。”阿楚抱住陈娴的胳膊。
“往者不可谏,来者犹可追。”我道,“您与慕容家有旧怨,陈叔和婶子对慕容家也有新恩,成国侯怎么办,我们无法干涉,但一定要做好应对的准备。”
陈夫人点头表示认同:“当日我与夫君救了他,他千恩万谢,极诚恳的表示必将厚报,但后来却再未提起此事,而此人并不是重利轻诺的性情,因此我推测,他或许的确知道了些什么,但他又并未动作,或许他心中也有所纠结。”
“对了娘,此事是否需要知会古家夫妇他们?”阿楚在冷静下来后,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,“按说此事知晓者不宜过多,但如果真有麻烦找上门来,辛夷她们毫无准备提防就更加危险了。”
“楚儿说的有理。”陈武师道。
陈夫人道:“既是一条藤上的蚂蚱,通个气也是好的,就怕消息走漏更多。”
我道:“古家夫人与婶子本是旧交,辛夷和孙仲景更别说了,知道的只会更多不会更少,这种时候瞒着也没什么意思,还显得生了隔阂一般。”想了想后我又补充道,“不过,成国侯那边,化守为攻或许也是个法子。”
陈娴最终一锤定音:“好,既如此,便请大家来管住自己的嘴罢。”想了想又补充道,“古慎还是算了,象征性的瞒下他吧,他到底是古家二公子,知道越多越容易被人捏住把柄。”
华国150年十二月二十三,冬至日,成国侯京中府邸。
今年的冬雪直到冬至方才造访华国,侯府外雪片翻飞,府中室内早已燃起炭火,一片暖意融融。
慕容钦正端坐于书房内查看一本山川图志,时不时低低咳嗽几声,下人却突然来报:“公子,英国公府的四公子来了。”
“请他直接来书房罢,跟他不用讲究那么多规矩。”慕容钦头也没抬,提笔在案上的图册上批注起来。
“连杯茶都得我自己倒,慕容侯爷,您府上贵客还有几个有我这般待遇?”顾辰逸端了两杯茶自走进门来,顺手将其中一杯推给伏案苦读的那位。
“多谢,若是你三哥同来,他还能从厨房给我捎份茶点。”慕容钦放下笔,淡淡地道。
“其一,我未生第三只手,其二,我素来不大喜这些甜食,对不住了。”顾辰逸说着,顺势扫了一眼慕容钦正翻阅的书册内容,“《南梁湖山志》,看样子年后南境一带很需费些心力,你预备何时返回?”
“若非怡王心术不正,我也不必重孝在身的进京,还被严看了这些时日。”慕容钦道,“实不相瞒,看军中来信我已是归心似箭,但你也不是不知,我这身子一入秋冬是个什么光景,南境气候炎热还好些,如今……待开春再上路罢。”
见他神情落寞,顾辰逸不由叹气:“这些年听闻你求医无数,吃药调理不少,竟没有一桩顶用的么?”
“自小落下的病根,哪是这么容易好的?”慕容钦道,忍不住又咳起来,忙灌了两口热茶压下,“我只盼三件事,三年内能将南境海盗连根剪除,逼得南梁归顺,或还能为平南军选一位接班人。”
顾辰逸听懂了他的意思,劝道:“来日方长,你切莫多想。只是之前我便问你或可让然儿问诊一番,你为何坚辞不受?”
慕容钦笑了:“我记得你还未迎娶沈姑娘,如此你心中竟不生半点醋意么。”
顾辰逸笑道:“休提这话,我若为了这个说她,她怕是得给我连看不知多久的脸色。再者说,然儿的病人里不乏男子,我便是醋也醋不过来的。”
慕容钦点头赞许道:“沈姑娘是位奇女子,但我并不是为男女大防推拒,而是——”
他顿了顿,似乎是在组织语言:“我应是找到了当初伤了我父亲的仇家之后,但他们却在不久前对我出手相救,我一时不知是该报恩还是报仇了。”
顾辰逸斟酌了一下,道:“那在你看来,旧恨新恩孰轻孰重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