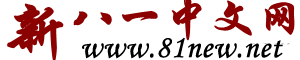第一卷 笼中雀 第六十一章 过河卒
作品:《剑来》 惹祸精妇人一走,没了春光乍泄的风景可看,杨家铺子的人群也就很快散去。
郑大风缩头缩脑跑到正屋檐下,蹲在远处,不敢离杨老头太近。
同样是徒弟,他和李二在这个师父面前,待遇是云泥之别。
郑大风也怨师父偏心,只不过有些事情,实在是不认命不行。
郑大风怯生生问道:“师父,齐静春是铁了心要不按规矩来,到时候咱们何去何从?”
老人一言不发,抽着旱烟,一头黑猫不知何时何处到来,蹲在老人脚边不远处,抖了抖毛皮,溅起许多雨水。
郑大风忧心忡忡道:“真武山那厮竟然请神下山,会不会有麻烦?毕竟现在有无数人盯着这边呢。”
老人依然不说话。
习惯了自己师父的沉默寡言,郑大风也不觉得尴尬,胡思乱想着,又想起了齐静春,咒骂道:“他娘的你齐静春当了五十九年的孙子,还差这几天功夫?读书人就是死脑筋,不可理喻!”
老人终于说话:“你不读书也是死脑筋。”
郑大风不以为耻,转头谄媚道:“要不要给师父你老人揉揉肩敲敲腿?”
老人淡然道:“我没什么棺材本,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”
郑大风赧颜道:“师父你这话说的,伤人心了啊,我这个做徒弟的,本事不大,可是孝心足啊,哪里会惦记那些,我又不是李二他媳妇。”
老人嗯了一声,道:“你比她还不如。”
郑大风整张脸都黑了,耷拉着脑袋,霜打茄子似的,没有半点精气神。
不过他猛然间满脸惊喜起来,才发现师父今天说的话,虽然还是不堪入耳,可好歹说了这么多,难得难得,等回到东边屋子那边,可以喝一壶酒庆祝庆祝。
郑大风心情愉悦几分,随口问道:“师兄拦得住那家伙?”
这次不等老人拿话刺他,郑大风自己就扇了自己一耳光,“师兄拦不住才有戏,要真拦下来,以后就真要喝西北风了。”
老人莫名其妙问道:“郑大风,你知道自己为什么没大出息吗?”
郑大风愣在当场。
心想师父这个问题大有玄机啊,自己必须小心应对,好好酝酿一番。
不曾想老人已经自顾自给出了答案,“人丑。”
郑大风双手抱住脑袋,望向院子里的雨水四溅,这么个老大不小的汉子,欲哭无泪。
————
衙署管事都不用怎么察言观色,就知道自己不适合继续待下去,随便找个由头离开屋子。
陈松风继续埋头查阅档案,只是相比较陈对在场时的战战兢兢,总算恢复几分世家子弟的潇洒气度,但越是如此,一旁看在眼里的刘灞桥就越觉得气闷,一肚子憋屈不吐不快,只是性子耿直是一回事,口无遮拦又是一回事,刘灞桥便想着也出去散散步,眼不见心不烦。
陈松风突然抬头笑道:“灞桥,终于坐不住了?”
刘灞桥刚从椅子上抬起屁股,闻言后一屁股坐回去,气笑道:“呦呵,还有心情调侃我,你小子胸襟气度可以啊。”
陈松风放下手中一本老旧籍书,苦涩道:“让你看笑话了。刚才为我打抱不平,我并非不识好歹,只是……”
刘灞桥最受不了别人苦情和煽情,赶紧摆手道:“别别别,我就是瞧不上你家远房亲戚的欺软怕硬,我说她几句,纯粹是我自己管不住嘴,你陈松风不用感恩戴德。”
陈松风后背向后仰去,轻轻靠在椅背上,轻轻呼出一口气。
这要是在龙尾郡陈氏家门,仅凭这个透着一股懒散的坐姿,给长辈一经发现,无论嫡庶子,小孩子一律要挨板子,成年人则要挨训。
豪阀世族的读书人,虽然往往被武人讥讽为道貌岸然,装腔作势。
可规矩就是规矩,打从娘胎生下来,就走在既定的道路上,大大小小的士族子弟,无一例外,从小耳濡目染。
当然,也有盛产清谈名士和荒诞狂士的南涧国,以言行不拘泥于礼仪,著称于世。
刘灞桥问道:“你和陈对到底什么关系,至于如此畏惧她?如果涉及家族机密,就当我没问。”
陈松风站起身,去关上屋门,坐在原本管事的椅子上,轻声反问道:“刘姓少年的买瓷人名分,几经波折,最后辗转到我龙尾郡陈氏手中,你就不好奇是为何?”
刘灞桥点点头。
恐怕搬山猿打破脑袋也想不到,因为那部剑经闻风而动的竞争对手,竟然不是死敌风雷园,而是横空出世的龙尾郡陈氏。
陈松风面容疲惫,应该是一路行来长期郁结,多思者心必累,终于忍不住要找个人吐吐苦水了,加上他深信刘灞桥的人品性情,所以缓缓说道:“虽说我们陈氏与你们风雷园关系更近,但陈氏子孙恪守祖训,不掺和山上山下的恩怨,已经坚守这么多年,难道一本对于陈氏子弟十分鸡肋的剑经,就能够让我们为此破例?陈氏是书香门第,不是修行世家,趟这浑水,有何意义?”
刘灞桥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了想,“是那个陈对的家族,想要将这部剑经收入囊中?难不成她家是哪个不出世的剑修豪族?”
陈松风摇头道:“并非如此。先前你也薛管事提及,小镇陈氏分两支,陈对就是属于最早迁出去的那一支,走得很彻底,干脆连东宝瓶洲也不待了,直接去了别洲,经过一代代的繁衍生息,开枝散叶,陈对所在家族,如今已经被誉为‘世间坊楼之集大成者’。当然,这些消息,在东宝瓶洲从未流传,我们龙尾郡陈氏也只是因为与他们有丁点儿渊源,才得以知晓内幕。”
刘灞桥嗤笑道:“是那娘们吹牛不打草稿,还是欺负我刘灞桥没学问?她家能有功德坊?”
陈松风伸出两根手指。
刘灞桥白眼道:“听清楚了,我说的是功德坊,不是功名坊!”
陈松风没有收起手指。
刘灞桥有些吃瘪,继续不服气问道:“那学宫书院坊,她家能有?!”
刘灞桥所谓的学宫书院坊,自然是儒家正统的三学宫七十二书院,绝非世俗王朝的普通书院。
偌大一座东宝瓶洲,不过山崖、观湖两座书院。
陈松风缓缓收起一根手指,还剩下一根。
刘灞桥佯装要起身,双手撑在椅子把手上,故作惊慌道:“我赶紧给那位姑奶奶道歉去,我了个乖乖,就这种蛮横不讲理的身世,别说让你陈松风翻几本书,就是让你做牛做马也没半点问题嘛。”
陈松风笑而不语。
这大概就是刘灞桥的独有魅力,能够把原本一件憋屈窝囊的糗事,说得让当事人完全不生气。
刘灞桥扭了扭屁股,双臂环胸,好整以暇道:“好了,知道那位祖宗奶奶的吓人来历了,你接着说正题。”
陈松风笑道:“其实答案薛管事也说了。”
刘灞桥灵光一现,“刘姓少年的祖上,是陈对那一支陈氏留在小镇的守墓人?”
陈松风点头道:“孺子可教。”
刘灞桥咦了一声,“不对啊,刘姓少年家祖传的剑经,不是出自于正阳山那位叛徒吗?当然了,也算是我们风雷园的祖师之一,不管如何,时间对不上,怎么能够成为陈对家族的守墓人?”
陈松风解释道:“我可以确定,刘家最早正是陈对家族的守墓人,至于后来躲去你们风雷园的那位剑修,最后又为何来到小镇,成为刘家人,还传下剑经,估计有一些隐晦内幕吧。所以最后传家宝成了两样东西,剑经加上瘊子甲。至于陈对,她其实志不在宝物,只是来祭祖罢了。在此之外,如果刘家人还有后人,无论资质如何,她都会带回家族倾力栽培,算是回报当年刘家老祖的守墓之功。”
刘灞桥一脸匪夷所思,“那么大一个家族,就让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来祭祖?然后搞得差点被那位大骊藩王一拳打死?陈松风,我读书不少的,虽然多是一些床上神仙打架的脂粉书,可确实由此领悟到了好多人情世故,所以我觉得那娘们肯定是个假冒货!”
陈松风摇头苦笑道:“那你是没有看到我祖父见到她后,是何等……客气。”
为尊者讳,所以陈松风实在说不出口真相,只能以“客气”二字含糊形容。
家族为她大开中门,家主对她一揖到底,举族上下将她奉为上宾,接风宴上让她来坐主位。
这一切对陈松风的冲击之大,可想而知。
刘灞桥疑惑道:“那刘姓少年,不是差点被那头老猿一拳打死了吗?”
陈松风叹了口气,“你自己都说了,是差一点。”
陈松风起身来到窗口,窗外暂时斜风细雨,只是看天色,像是要下一场滂沱大雨。
陈松风轻声道:“那位阮师,好像与陈对的一位长辈是旧识,曾经一起行走天下,属于莫逆之交。”
刘灞桥试探性问道:“你是说阮邛能够接替齐静春,坐镇此地,陈对家族是出了力气的?”
陈松风淡然道:“我可什么都没有说。”
刘灞桥啧啧称奇。
难怪这个娘们面对宋长镜,也能如此硬气。
远在天边的家族威势,近在眼前的圣人庇护,她能不嚣张吗?
刘灞桥突然问道:“说说看本命瓷和买瓷人的事情,我一直挺感兴趣的,只可惜咱们风雷园不兴这一套,直到这次被师父强行拉来当壮丁,才粗略听说一些,好像现如今咱们东宝瓶洲,有几个声名赫赫的山顶人物,最早也是从这座小镇走出去的?”
陈松风略作犹豫,还是选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,泄露天机道:“有些类似俗世的赌石,每年小镇大概有三十余婴儿诞生,三十座龙窑窑口按照交椅座位,依次选择某个孩子作为自家龙窑的‘瓷器’,打个比方,今年小镇生下三十二个孩子,那么排名最前面的两座龙窑,就能有两只瓷器,如果明年只有二十九个新生儿,排名垫底的龙窑,就意味着只能一整年没收成了。”
“所以小镇土生土长的人,都有自己的本命瓷,如今在本洲风头无二的曹曦谢实两人,一位有望成为天君的道教真君,一位杀力无穷的野修剑仙,也不例外。虽然小镇这座鱼塘相比外边,已算是极其容易出蛟龙,但是化龙的代价巨大,这些‘瓷器’,一旦成功跻身中五境后,生前不登上五境,是注定没有来生的,魂飞魄散,生生世世,万事皆休,恐怕连道祖佛祖也奈何不得。而在这期间,就会被买瓷人抓住致命把柄,生死操控于他人之手,任你是曹曦谢实这般人物,一样如此。”
“话说回来,等到成为曹曦谢实这样的通天人物,买瓷之人自会恨不得当祖宗供奉起来,哪里敢以瓷器主人自居。毕竟是互利互惠的事情,任何一个家族,能够拥有曹曦谢实这样的战力,睡觉都能踏实,理由很简单,平时小事,兴许请不动他们的大驾,但是涉及家族存亡之际,他们肯定要来助一臂之力,不愿为我的家族作战,可以,那我就打碎你的本命瓷,大伙儿一起玉石俱焚便是。”
刘灞桥听得叹为观止,难怪大骊王朝在短短两三百年间,崛起迅猛,已经形成了吞并一洲北部疆土的恢弘气势,刘松锋听得入神,干脆就盘腿坐在椅子上,用手心摩擦着下巴,问道:
“我知道小镇女孩六岁,和男孩九岁是一个大门槛,与我们修行是一个道理,在那个时候能够知晓未来修行成就的高低了,如果说在那个时候,买瓷人来小镇带走大道可期的孩子,那么那些不成器的瓷器呢?那些赌输了的小镇孩子,他们不值钱的本命瓷,各大龙窑又该如何处置?”
陈松风轻声道:“会被拿出龙窑,当场敲碎丢弃,小镇外有一座瓷山,就来源于此。”
刘灞桥心中隐隐不快,问道:“那些孩子的下场如何?”
陈松风摇头道:“不曾听说过,估计不会好到哪里去。”
刘灞桥叹了口气,抬手狠狠揉了揉脸颊。
这一桩由各方圣人亲自敲定规矩的秘事,绝不是他小小风雷园剑修能够指手画脚的。
可年轻人就是觉得有些不痛快。
长久沉默,最后刘灞桥轻声道:“如此说来,从这里走出去的家伙,人人都是过河卒。”
陈松风跟着说道:“修行路上谁不是?”
刘灞桥心有戚戚然,点头道:“也是。”
————
屋门吱呀一声轻轻打开,脸色微白的草鞋少年蹑手蹑脚跨过门槛,转身轻轻关上木门。
也学着杨老头搬来一条小板凳,坐在台阶上,雨点大如黄豆,天色昏暗如深夜,只是不知为何,这么大一场暴雨,打入屋檐下的雨点反而不多,老人坐了很久,衣衫上也不过是有些许水气而已,陈平安十指交错,安静望向院子里积水而成的小水塘。
老人抽着旱烟,大团大团的烟雾弥漫四周,只是檐下烟雾与檐外雨幕,井水犯河水。
好像天地间存在着一条看不见的线。
老人不讨厌这个孩子的最大一个原因,就是孩子不管什么情况,都不会胡乱嚷嚷,不会吵到自己。能不说话烦人,就绝不开口。
孩子这一点,跟徒弟李二很像。
郑大风就差太远了。
陈平安轻声道:“杨爷爷,这么多年,谢谢你。”
老人皱眉道:“谢我?如果没有记错,我可从来没有白白帮过你,哪次缺了报酬?”
陈平安笑了笑。
就像杨老头当年答应自己给杨家铺子上山采药,然后低价购买的同时,药铺里许多草药也低价卖给陈平安。看似公平,其实陈平安心知肚明,这就是最实实在在的帮忙。
再还有,一支自制的竹烟杆子,值得了几个钱?
但是陈平安能够这么多年坚持下来,一年到头无病无灾,很大程度上,靠的都是杨老头当年传授的那套呼吸法子。
老人抬起头,望向天空,讥笑道:“别人施舍一点小恩小惠,就恨不得当做救苦救难的菩萨,尤其是大人物从牙缝里抠出一点渣滓,就格外感恩戴德,甚至自己都能被自己的赤子之心感动,觉得自己这是知恩图报,所以是醇儒忠臣、是某某某的得意门生,美其名曰士为知己者死,一群忘本的混账王八蛋,当初就不该从他们娘胎里爬出来……”
陈平安挠挠头,有些忐忑,不知道杨老头是不是在说自己。
老人收回视线后,漠然道:“不是说你。”
陈平安突然看到一个熟悉身影,于是有些发愣。
正堂后门有回廊屋檐,一位双鬓霜白的中年儒士撑伞而至,一手持伞,一手拎着长凳,穿过侧门后,将长凳放在廊中,坐下后把油纸伞斜靠在凳子旁,然后双手拍了拍膝盖,端正坐姿,最后笑望向后院正屋檐下的老人和少年,温声道:“山崖书院齐静春,拜见杨老先生。”
儒士脚上的靴子被雨水浸透,沾染淤泥,袍子下摆也是如此。
老人意态闲适,用烟杆指向那位此方圣人,“你来的第一天,我就知道是个不得志的,不过这么多年处下来,没听到你半句牢骚,也是怪事,你齐静春可不像是唾面自干的人物,所以这次你失心疯,估计外边有些懵,我倒是半点也不奇怪。”
齐静春伸手拍了拍肚子,微笑道:“牢骚有啊,满肚子都是,只是没说出口而已。”
杨老头想了想,“你的本事我不清楚,不过你家先生,就凭他敢说出那四个字,在我眼中就能算这个。”
老人伸出大拇指。
齐静春苦笑道:“先生其实学问更大。”
老人讥笑道:“我又不是读书人,你先生学问就算已经大过了至圣先师,我也不会说他半句好。”
齐静春正色问道:“杨老先生,你是觉得我们先生那四个字,才是对的?”
老人哈哈笑道:“我没觉得对,只是之前世间所有衣冠之辈,皆信奉之前四字,看得我心烦,所以有人出来唱反调,我便觉得解气,仅此而已。你们读书人自己打擂台,打得斯文扫地,满地鸡毛,我高兴得很!”
齐静春失声而笑。
齐静春刚要说话,已经会意的老人摆手道:“客套话莫要说,我不爱听,咱们就不是一路人,一代代都是如此,别坏了规矩。再说了,你齐静春如今就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,我可不敢跟你攀上交情。”
齐静春点点头,起身跟陈平安招手道:“用你送去的蛇胆石,刻了两方私章,一隶书一小篆,送给你。”
陈平安冒雨跑过水塘似的院子,站在齐静春身前,接过一只白布袋子。
齐静春微笑道:“记得收好。以后看到了心仪字画,例如一些觉得气象不俗的山河形势图,可以拿出印章往上一押。”
陈平安迷迷糊糊点头道:“好的。”
杨老头瞥了眼少年手中的袋子,问道:“那个春字呢?”
齐静春笑道:“早先刻了一方印章,送给赵家一个孩子。”
老人笑道:“你齐静春是善财童子啊?”
齐静春对于老人的调侃,不以为意,告辞离去。
看到少年像一根木头杵在原地,杨老头气笑道:“白拿人家东西,就想着蹦蹦跳跳回家钻被子里偷着乐呵?不知道送一送齐先生?”
少年赶紧跑向正堂后门,老人笑骂道:“带上伞!你现在这身子骨,经得起这风吹雨打?”
陈平安跟店铺伙计借了一把伞,跟上齐先生,一起走在大街上。
老人始终坐在檐下抽着旱烟,烟雾缭绕。
想起那两方私印,虽然犹在袋中,可是杨老头察觉得到其中端倪,所以才有“春”字一问。
方寸之间,大是壮观。
没过多久,草鞋少年就回到院子,杨老头问道:“最后说了啥?”
陈平安叹了口气,坐回小板凳上,“齐先生说了一句话,说君子可欺以其方。”
杨老头闷闷道:“立在文庙里的那帮老头子,脑子坏了吧,明摆着有人在针对山崖书院和齐静春,还一直袖手旁观,真当自己是泥塑木雕的死东西啦?”
陈平安没听清楚,问道:“杨爷爷,你说什么?”
老人默不作声。
好一个不做圣贤做君子。